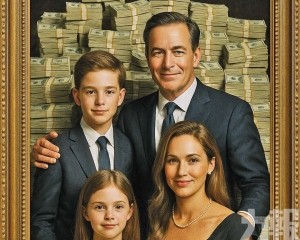2025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再次為澳門拉響警報:新生嬰兒共1,421名全年新生嬰兒人數預計將跌破2024年已經極低的3,607人。這個數字,意味著澳門未來正以每名婦女將小於0.58的驚人低度,穩坐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冠軍」寶座。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此前在立法會的警告言猶在耳——澳門將在五年內正式進入「超少子化」階段。這不僅是數據的警示,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預警,揭示出經濟補貼與政策鼓勵在根深蒂固的社會心態與結構性困境面前的無力。
要理解為何每月1,500澳門元的生育補貼乃至各種家庭友善政策均告失效,必須深入探究澳門Z世代(約生於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的集體心理圖景。
這一代人在「核心家庭+外籍家傭」的典型模式中成長,作為家庭關注的唯一中心,他們是「被照顧者」,卻極少機會學習成為「照顧者」。他們親眼見證了父母為育兒付出的巨大代價:個人生活的消亡、長期的疲於奔命以及在狹窄居住空間中的孤立無援。這種成長經歷,在他們潛意識中刻下了一個牢固的等式:生育 = 失去自由 + 承受壓力。
與此同時,Z世代是個人主義與數字化生存的原住民。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構建的「理想生活」範本是精緻、有序、可控的,而養育孩子則意味著混亂、噪音與無限的責任。這種「審美上的不兼容」,使他們在情感上對生育產生了根本性的拒斥。對許多Z世代女性而言,高等教育的洗禮與職業生涯的追求,更讓她們無法接受傳統性別角色所帶來的自我犧牲。
「不兒童友好」的社會生態系統
澳門的社會環境,從物理空間到競爭邏輯,正在系統性地「勸退」生育。
在物理層面,城市化進程催生了對「安靜」與「秩序」的極致追求。商場、餐廳、公共交通等公共空間對孩子的哭鬧與奔跑容忍度極低,無形中傳遞出「兒童不受歡迎」的信號。在社會層面,由升學主義主導的「投資型育兒」模式,讓Z世代自身就是惡性競爭的產物。他們深知在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戰場上養育後代的巨大成本與精神損耗,從而理性地選擇「不開始,就不會後悔」。
澳門的超低生育率,是本世紀初特定社會文化孕育出的「苦果」。壓垮生育意願的最後一根稻草,並非單一的經濟壓力,而是由家庭結構變遷、個人主義興起、競爭性社會生態與宏觀環境不安共同編織的一張大網。企圖逆轉這一趨勢,絕非依靠更優厚的生育津貼就能實現。它需要一場徹底的社會文化重塑:從建設真正「兒童友好」的城市公共空間,到反思並改革功利主義的教育競爭模式;從推動企業落實真正的家庭友善工作制度,到在社會層面重建對家庭與養育行為的價值認同。這條路遠比開支票困難,但卻是澳門面對這顆「計時炸彈」唯一可能的出路。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青委副主任黃旭華